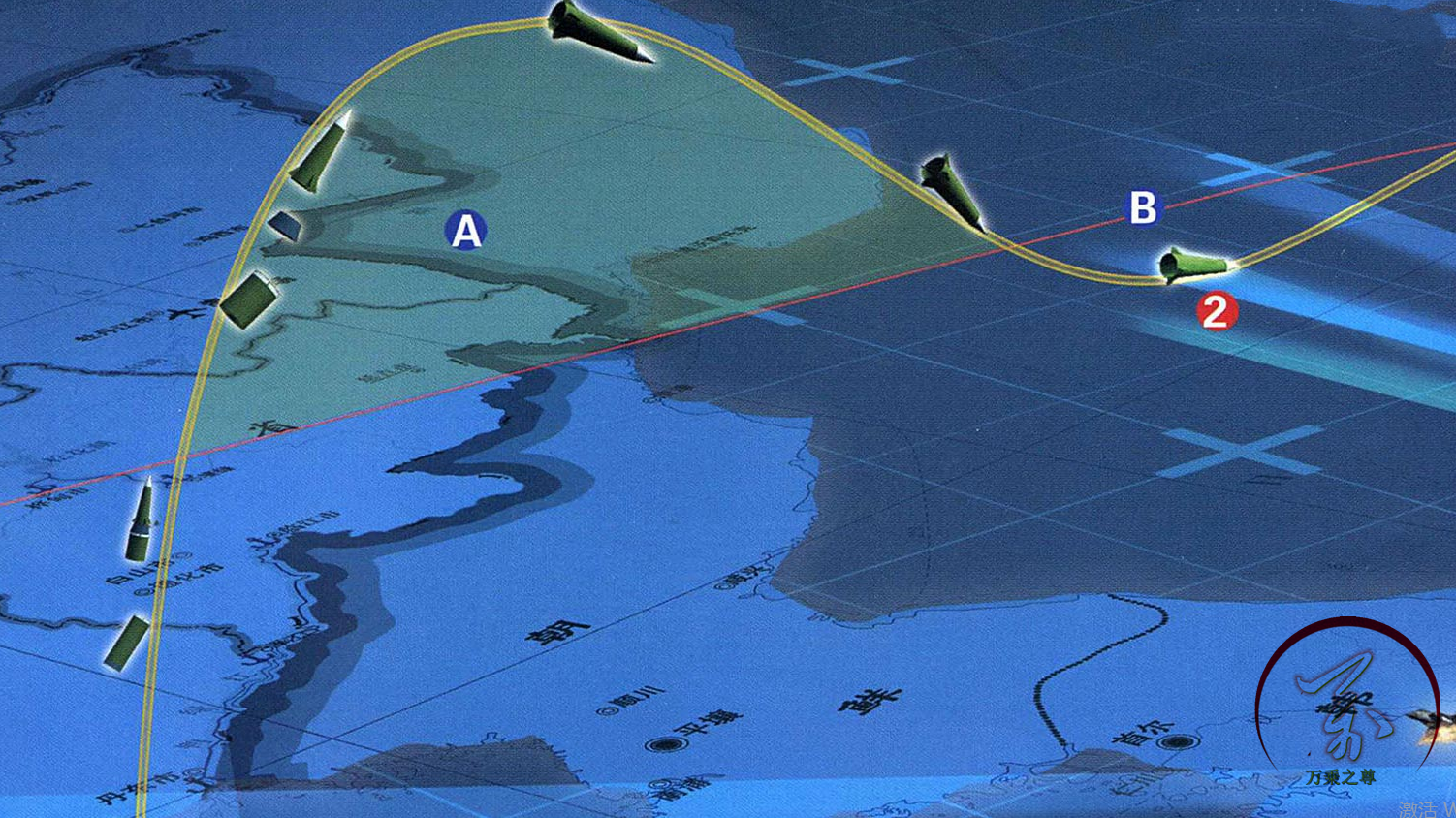丽娟和亚平婚后,基本上就是丽娟奴役着亚平,在她手里拿着遥控器一通乱按时,就扯着嗓子让亚平帮她倒水,而亚平也赶紧端水过来,还不忘嘱咐说太烫等下喝。诸如替她洗脚不忘用毛巾擦脚,吃完饭从不让她洗碗,家里体力活都会亚平之类的,在小两口配合得严丝合缝的情况下,日子过得跟蜜里调油一般,羡煞旁人。
丽娟原就是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碰上好天气或是小草发芽这种常见的变化也要开心上一天,而且在弄堂里长大的她,自小就发愿一定要远离弄堂,住上敞亮的大房子,嫁一个有工作能力长得又高又帅的男人。而生在牡丹江亚平的出现,就完全符合她的审美和要求,虽是以“未婚先孕”哄骗自己母亲顺利出嫁,但她对眼下的幸福生活很满意。
尤其是亚平的父母远在老家,这对她来说既不用承受公婆的压力,又能跟自己父母同一座城市的小日子,几乎是每天都可以哼着歌过得。只不过上天是公平的,一般给了你一颗枣的甜蜜,就会在后面酝酿一场小的祸事让你心力憔悴。
公婆的到来就是罩在她头上赶也赶不走的一片乌云,属于她那50万的房子,自己父母给的10万嫁妆以及两人的3万积蓄加上贷款的35万,却都不及公婆给的2万,因为这2万不仅是公婆入住的敲门砖,更是亚平赋予公婆最高的掌家权,和堵住她反驳最有力的筹码,以及敲响她搭上性命的丧钟。
亚平妈给的2万,被亚平当成改变时运的杠杆。自他们入住新房的一年半来,亚平对自己父母出的2万已经到了几近疯魔化的程度。因为在他心里这不仅仅是2万,而是以小博大的历史性不可替代的转折,更是四两拨千斤的胜利,也是他们得一辈子感恩戴德地铭记于心的大事。
原著里,亚平不止一次说:“房子就算是股份公司吧!你们二老也是最初的大股东啦!等我们一弄好你们就过来玩儿吧!想住到啥时候就住到啥时候,这原本就是你们的家,有这两万块钱,客厅的地都铺满啦!”
因为他们凑够了15万的首付,就可以提早在世博会选址之前买,而不用憋屈地买西头的二楼,也不用买对面那套没人选的库存房,更不会等隔三条横马路那片荒地南汇县待开发的房子。总而言之,亚平父母给的2万太及时了,如果没有这2万,他们就没有幸福可言。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有这样一段:五十度气温下的正午,只有烈日将一排排建筑短短的影子照射在空寂的街道上,整个小镇好似死去了一般,时间在这里也凝固起来了。
亚平妈这2万块就如那五十度的高温一样,一直炙烤着亚平,让他一遍遍被自我限定父母伟大的感情里冲刷,更成了他刻意模糊丽娟的10万嫁妆,以及他俩自己凑的3万的事实。仿佛只有无限放大父母的给予,才更能体现他的孝顺,以及2万带来的杠杆作用。
这也让看不到实物的亚平父母却能凭空想象儿子的新家,灯是他们买的,地是他们买的,门是他们买的,家具是他们买的,连油漆钉子把手镜子沙发靠垫儿,反正凑起来只要能以两万作为单位的东西,都是他们掏的钱。
更不由地加深了亚平对父母的感激以及自我内心的愧疚,甚至让丽娟也觉得有一种心虚的感觉,让她打心底怀疑这个家的一根线一块砖都不是自己省出来的。
心理学家威廉杰姆斯曾说过,人性最深层的需要就是渴望别人的赞赏,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
这句话里的“别人”大多是指父母,因为无论是多成功的人,或多有名的人,他们穷其一生得到的财富和声名,都不及父母对自己的一声称赞,那会是一种从内到外的舒展,也会是一种从头到脚的满足。
亚平对父母的感激不仅宣于口,更体现在行动上,一会怕地滑一会怕灯光太暗,总而言之就是那种刻意奉承故意迎合,像极了巴结领导上司的丑陋嘴脸。更可笑的是,他的父母也沉浸在这看起来母慈子孝的自我陶醉里,殊不知这种浮于表面的亲情,本身就是对亲情的一种践踏。
亚平妈给的2万,是亚平堵丽娟嘴的最大筹码。丽娟对亚平这种刻意迎合自己父母的做派是嗤之以鼻的,但亚平的出现也成功让她摆脱了自己弄堂里的父母,以及自小就立志最不愿嫁的上海小男人。尤其是亚平酷似陆毅的外表让她脸上有光,而且从小地方出来的男人都会倍加疼爱老婆,公婆离自己又远,也不用担心家庭问题,总结来说,她对亚平很满意。
虽然在她相中亚平的年代,最流行的是找个老板、美国绿卡或小开,能顺利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她也清楚地知道物质富裕的背后藏不住的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内里,今天领回来一个女人,明天带回来一个私生子的污糟事。
更不像有些上海男人,整天追在屁股后面大事小事都要问,连卫生巾都塞到老婆包里,诸如晚上几点回来,谁又给你打电话了,那个冲你笑的男人你认识吧,夜里吃点啥等等。而她找的亚平则是个给了她绝对自由的空间,哪怕知道有男人找,也只是递过来连多一句都不问的大男人。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
她找到亚平做丈夫,就是人生的第一次觉醒,因为她没有被小男人跟在屁股后的烦恼,也没有担心丈夫出轨不着调的忧愁,就婚后亚平对她的体贴照顾和温柔强大地保护,都说明她这次婚姻的命运是正确的。
只是她太沉浸在亚平好的幻境里,在一次次强调父母支援的2万时,在对父母的刻意迎合时,她幻境里的亚平就已经变了味道,或者说是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婆媳相处从来都是一门学问,而处在中间的丈夫不说做好端水大师,但保持中立是最基本的操作,而亚平却没有,他的一腔热情贴向父母,独留还未认清现实的她。
王小波的《红拂夜奔》里说,这一切告诉我说,不能拿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当真,不能拿别人当真,也不能让别人拿我当真。
正如母亲对她炫耀婆婆如何和善的忠告一样,“对你千日好,不如人家一个笑。我就希望以后你可别哭着回来找我就行了。你是没吃过婆婆的苦头。你要真命好,倒是我前世修的福,就怕是个笑面虎,吃你都不吐骨头。”
明明是她前一晚上努力收拾了6个小时的家,却在婆婆一进门那句“这家可够乱的啊!”就全盘否定了。是了,这才是真正婆婆的面孔,一个女人成婚前后在婆婆那里得到的永远都是两副面孔。
婚前总爱拉着手热切地问你“冷不?饿不?累不?”还不忘装腔作势地教训自己的儿子,“这么标致的一个媳妇,又俊又疼人儿,还是上海闺女,你可不能慢待了人家,我不答应啊!丽鹃是个好闺女,我中意!”婚后就变成了儿媳这种生物,不是用来奴役就是拿来教训的。就像她婆婆那股拆出大包小袋摸到合适的空间塞进去的利落劲,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一家之主的位置上。
这个世界既真实又现实,真实的是从来不把任何一个人当回事,毕竟几十年的光景后都得尘归尘土归土;现实的是你不会把别人当回事,更不能天真地让别人拿自己当回事。一旦你违背了任何一条,即将到来的结果不是天崩地裂就是雷雨交加。
而这一切都是被魔化亚平父母给的2万,以及她自身的不以为然造成的,只不过在这个还没来得及建立多少亲情温情的重组家庭里,却没有任何一人指出事情的对错,或对边界的判断。
历来都是边界不清的人,善恶也不会分。
知乎上有一个问答:如何理解人善被人欺?有一个回答是,人善被人欺中的善,并不是真正的善良,而是界限感不清,原则性不强,善良不是无底线。
丽娟只一味地沉浸在亚平的好里,却没有建立好和亚平父母的边界,婚姻虽是两个家庭的事,但婚姻生活却是小两口自己的日子。任何一方父母的参与,都会引爆或大或小的家庭战争,因为每个父母最爱的都只是自己的孩子,而别的孩子再好也好不到他们的心坎里。
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从来都不是你对我好,我便对你好,而是你清楚我的底线,我清楚你的边界,在握手言和的时候,也不让惊醒人和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这个事实。而独立存在的个体,就是组成能存活于世不败之地的根本。看似每个人都可以相互联系,却又不能替代另一个人而存在。